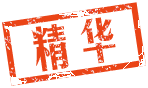虽然我是家里惟一的女孩,父亲却好像从来没有对我显出过特别的喜爱。在地里干活,偶尔捉只小兔或鸟儿,回来也是送给两个哥哥。
小学在父亲的不经意间过去了,上学和放学就像他的出工和收工一样,只是顺其自然的事。他不关心我,就如我不关心他的收成。
可是,我考上了镇上的三中。这就意味父亲的大半收成都得被我一个人用掉。母亲望着父亲逐渐弓起的背,幽幽地说:“要不,别让女儿上学了?”父亲脸上刀刻的皱纹突地一跳:“哪能?再难也得让她上学!”
在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,父亲一头挑着我的行李,一头挑着一筐桃子,送我去上学。跟在父亲背后,望着颤悠悠的扁担和父亲那被扁担磨出老茧的双肩,我又一次被感动了,在心里默默发誓——不学出个样子来,无颜面对父亲。
到学校门口,我一个人进去,父亲则去卖那筐桃子。等我安排好住宿后去集市找他,父亲已经走了。我想,他肯定是饿着肚子走的,翻山越岭,还得走20里路啊!
读初中的三年里,我很少回家。父亲总是隔三差五地给我送干粮和桃子,当然都是些歪七扭八卖不出去的小桃。
冬天天短,父亲每次来都得起个大早,见到我,往往是胡须上结了一层白霜,掏出母亲烙的白面饼,硬邦邦的全是冰碴儿。中午,我们父女俩把饼泡在开水里,就着父亲带来的咸菜,吃得有滋有味。夏日,父亲捎带着卖桃,20里的山路,父亲的脸膛晒成了酱紫色。赶到学校已近中午,我把早已凉好的白开水递过去,父亲一气儿就喝一大缸子。父亲向来是当天来当天走,三年里,他走了几十年也走不完的路程。
三年后,我考到了县城高中,父亲挑着扁担送我去上学,安排好住宿已经很晚了。我要送父亲到学校招待所去住,他说什么也要自己去,说他怕我回来时找不到自己的宿舍。我知道,那样父亲会一夜都不安心的,所以也只好随他去了。下过雨后,气温骤降了许多,加上一天的颠簸,实在是太累了,我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突然,辅导员老师把我叫醒,她说,我父亲为了省15元的住宿费,竟然睡在外面的水泥乒乓球台上。
我急急起床出门,扑到父亲身边,同宿舍的七姐妹哽咽着说:“让伯父就住在我们宿舍,我们可以两个睡一张床!”
“可是你们是女生宿舍呀!”辅导员老师阻止,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。“那又怕什么,他是父亲啊!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。
作者:廖思思 来源:现代女报